文/邱文通 照片/許益超
「童年的自己,是個很安靜的小孩。」他說道,不是那種害羞膽怯的沉默,而是一種與世界低聲交談的靜。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許益超記得,那時候,他常常一個人坐在窗邊,膝蓋抱著下巴,聽著窗外的風吹過樹梢、鄰居家鍋碗瓢盆的碰撞聲,還有母親在廚房切菜喀、喀、喀的節奏,每一下都規律、溫柔,彷彿在提醒他:媽媽在家,一切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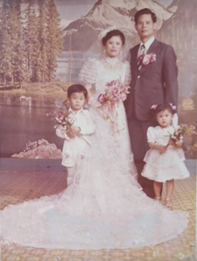

童年記憶中的聲音
「那時還不懂什麼是聲音的意義,但我知道,有聲音,就是活著的證明。」他輕聲說,語調像是在回味一段遠方飄來的記憶。
直到多年後,那些聲音在生命中突兀地沉靜下來。大學時期,母親罹患癌症,接受化療。在台北求學的他,每天傍晚都會在宿舍樓下的公共電話亭排隊,只為打一通電話回家。這是母子倆最深的牽繫,彷彿那條話筒線,能把他的聲音穿越城市、繞過病痛,輕輕落在母親耳邊。
但有一天,母親的聲音在電話那端忽然變得遲疑而模糊:「我……聽不太清楚你在說什麼了……。」那句話像是一把無聲的剪刀,把兩人之間的聯繫線一刀剪斷。他在電話亭裡怔住了,站在嗡嗡作響的公用電話旁,彷彿整個世界突然變得寂靜。
「那不是一種聽不見而已,」他後來這樣形容那一刻,眼神微微發亮又透著一絲脆弱,「那是一種失去了聯繫的感覺,像是在茫茫人海裡,你叫了一聲,卻沒有人回應。」
那一瞬間,他才明白,聲音不只是一種物理震動,不只是耳膜感受到的波紋,它是一條看不見的線,繫住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與存在感。而那條線,一旦斷了,有些話,就再也說不出口了。
從那天起,「聽見」這件事,在他心中不再只是科學名詞,而是一種使命。就像種子落入心田,靜靜地埋下未來某天會發芽的希望。那顆種子,後來長成了一條專屬於耳朵的學術之路,也成為他將一生獻給聲音與連結的理由。
從中醫到再生醫學
他經常說,自己的學術旅程,其實是從母親的病床邊開始的。
那時的他,還是個研究所新鮮人,站在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的面試現場,面對教授的提問:「為什麼想讀這個科系?」他沒有準備好標準答案,卻在那一刻,脫口而出:「因為西藥的副作用太大了……。我想看看,中醫藥有沒有可能,讓像我媽媽那樣的癌症病人,不要那麼痛苦地走完一段路。」
說完的瞬間,他愣了一下。那並不是一個用來「說服」教授的回應,而是多年來壓在心口的真話,終於有了出口。母親罹癌後,化療的折磨像是吞噬生命的倒數計時器。她不是被病魔打敗的,是在每一劑藥物注入體內後,一點一點失去原本的她。那樣的無力感,讓他開始思考:如果不能阻止疾病,是否能減少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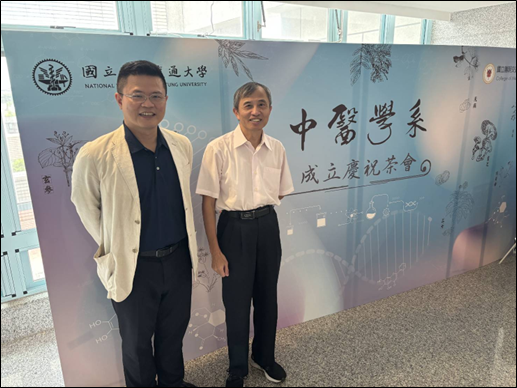
從那天起,他決定沿著中草藥的線索走進實驗室,一次又一次,在顯微鏡下觀察肝硬化與肝癌細胞的變化,想像著這些植物是否真的能柔和地改變什麼。那是一段紮實又孤獨的旅程。許教授回憶那段歲月時,語調總是低了些:「我一直希望,在那些片段的研究數據背後,可以找出一條更溫柔的醫療路徑。」
但時間推著他往更遠的方向走。他意識到,若要讓中醫藥的潛力被世界看見、聽見,就不能只停留在傳統框架裡。他需要一個語言,一個能與世界對話的語言,而那個語言,就是「分子生物學」、「幹細胞」、「動物模型」這些最前沿的醫學技術。
2005年那一年,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幹細胞中心成立,正在招募博士後研究員,而且是國防役名額。他記得自己投履歷的那天心情既期待又忐忑,沒想到順利被錄取,並由當時全球神經幹細胞領域的重量級人物邱英明教授親自面試。
第一次走進實驗室的那天,空氣中瀰漫著消毒水的氣味,那些精密儀器冷冷地閃著光,顯微鏡下的細胞一顫一動,彷彿有自己的語言。「我那時心裡想,這裡的每一個細胞,也許未來都能幫助某個家庭,留住某一段聲音或溫柔。」他眼神閃過一絲動容,「那不再只是研究,而是一種對未竟親情的修補。」
他的研究領域也從單純的中草藥,延伸到神經幹細胞、再生醫學,並持續探索耳朵、聲音、與記憶的關係。這條路,並不是當初規劃好的,也不是學術上的精算選項,而是一路走來,心裡那個年輕的他一直牢牢牽著母親的手,在默默走的路。
「我走進科學,是因為無法改變結局,但或許可以讓未來的某些人,不再重演那樣的痛苦。」他輕輕地說,像是在對自己,也像是在對過去那個瘦弱的母親道別。
那條從中醫走向再生醫學的路,最後他給了它一個名字,「以母親為名的學術之路」。不只是追求治癒,更是為了讓愛有一天能夠重新被聽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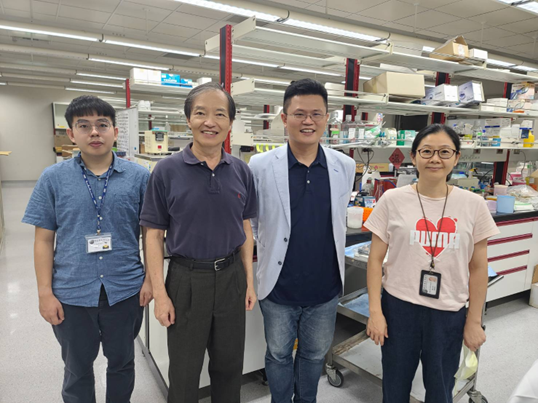

選擇「耳朵」的初心
許益超教授談起「耳朵」時,眼神會不自覺地發亮,語氣裡藏不住那種像是發現寶藏般的熱誠,那是他心中真正的熱點,一條不但繽紛、而且無人走過的科學秘徑。
「其實啊,我選擇耳朵,並不是因為它比較容易研究……。」他笑了笑,搖搖頭,語調中透著一種挑戰者的興奮。「剛好相反,是因為它太難了,太神祕,也太被忽略了。」
他曾細細觀察台灣的再生醫學發展:心臟、肝臟、神經、皮膚……各個領域早已高手雲集、研究百花齊放。只有耳朵,安靜得像被世界遺忘的角落。那是一片等待開墾的荒地,也是一個迫切需要有人先開口、先聽見的地方。
但真正讓他決定「就是它了」,其實還是一通電話,那通,他與母親通話中斷的電話。
那是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傍晚,他站在公共電話亭裡,一如往常地打給母親。兩人聊著聊著,突然她說:「我聽不太清楚你在說什麼了……。」那句話像是一道雷,劈開他心中最柔軟的地方。那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一種親密關係被割裂的痛楚,一種明明想靠近卻被迫遠離的無奈。
也就是在那個時期,他在研究纖毛轉錄因子時意外發現,它竟然與「聽覺細胞的分化」息息相關。那是一種令人心跳加速的連結,彷彿命運透過顯微鏡,向他眨了眨眼。
「那一刻我真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他興奮地說,「我覺得,好像宇宙偷偷告訴我,你該回到原點了,回到聲音,回到那通沒說完的電話,回到那個想讓媽媽重新聽見的自己。」
而就在他進入馬偕醫學院後,更驚喜地發現:這裡正好擁有全台灣最完整的聽力研究團隊,橫跨分子、臨床與病患現場,是一座等著被點燃的火種庫。他笑說自己就像一根剛好掉進火堆的火柴,一點就燃。
但許教授也不是只靠熱血。他是帶著戰略眼光進入這片空白市場的。他說:「這麼重要的器官,怎麼可以沒有學者研究?如果大家都在等,那就讓我來當第一個說『我來了』的人吧。」
他不只要人們重新「聽見」這個世界,更要讓那些被忽略的聲音、被壓抑的溝通、被迫沉默的情感,重新被世界「聽見」。
對他來說,耳朵不是器官,是一扇門,一道光,也是一條通往人心深處的路。而他選擇這條路,不只是為了科學的未知,更是為了那些還沒被聽見的愛與回應——他用全部的熱情,說出那句話:「耳朵,真的,太值得了!」



聽見,是愛的能力
許益超談起「聽見」,語氣總會慢下來。他的聲音不高,卻沉穩而有力量,彷彿他說的不是一個生理機能,而是一場靜靜發生在人心深處的奇蹟。
「聽見,其實是一種愛的能力。」他不只一次這麼說,語調裡混合著堅定與柔情。
他曾分享一個令他至今難忘的故事,那是一位來自國外、天生失聰的11歲男孩,因為罕見的 OTOF 基因突變,自出生起便活在無聲的世界裡。後來,在一項全球首例的基因治療實驗中,這個孩子成為首位受試者。治療完成後,所有人都在等,不是等待數據,而是那一個最簡單、卻也最難以預測的瞬間:這個孩子,能不能「聽見」。
某個平凡的早晨,孩子的母親,像往常一樣走近他,輕輕喚了一聲名字。那聲音不大,甚至有些微弱,但它穿過了沉默,越過了基因修復的邊界,悄悄地抵達了他的心裡。
男孩轉過頭來,眼神驚訝、凝視,像是第一次真正「看見」了母親。然後,他笑了。
那不是一個反射性的笑容,而是一種深刻的認出,是心靈與情感終於對上的那一刻。許教授說,那一刻的畫面非常安靜,卻比任何實驗結果都更有分量,「那不是一項治療的成功,而是一段關係的重建。」他語氣平靜,眼裡卻泛著光。
「我們做的,其實不是讓耳朵聽見而已,」他頓了頓,像是在慎重選擇每一個字,「我們做的,是讓人,重新有機會彼此靠近。」
對許教授而言,科技的最終意義,不是創新數據、不是登上期刊、甚至也不是某項技術的突破。他所追求的,是讓那些在沉默中擦肩而過的生命,重新連上線。讓失去回應的母親,終於能再次被孩子呼喚;讓孤單老去的父親,聽見兒女的笑聲再次進門;讓一場失語的愛,找到聲音的出口。
在實驗室裡,他操作顯微鏡、調控基因、設計模型;但在心裡,他始終記得,這一切的背後,是一個個活生生、有情感、有牽掛的生命。
「如果我們的研究,能讓一個孩子聽見母親的聲音,或讓一對老夫妻能在晚年還說得出『我愛你』,那我就知道,我們走對了方向。」他語氣平靜,眼中卻有溫度。
這就是他的科學觀:在分子與細胞的世界裡,找回人與人之間,最溫柔也最重要的連結。
學生踏上世界舞台
許益超教授從不把「教育」當作課堂上的教學任務,而是一場生命與生命之間的點燃。他談起學生時,語氣總會不自覺地放柔,眼神裡透出一種近乎父親般的關懷與期待。
那一年,他親自帶領三位馬偕醫學院的學生踏入哈佛醫學院附設的麻省眼耳醫院。那是一棟坐落在波士頓心臟地帶的學術殿堂,全球無數耳鼻喉科與聽覺醫學的重大突破,皆從這裡誕生。而那一天,站在那扇玻璃門前的,不再只是學術巨擘,而是幾位來自台灣的年輕學子,第一次,用自己的腳步站上這個世界級的舞台。
「老師,我從來沒想過,自己真的能站在這裡。」其中一位學生輕聲說道,眼裡閃爍著難以言喻的興奮與不安。許教授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語氣堅定又溫柔:「你們值得站在這裡。」
這句話,不只是鼓勵,更像是一個長年伏在他心中的願望,終於成真的見證。他記得自己年輕時也曾對這樣的地方懷抱渴望,但那時,資源稀少、機會難尋,那個夢始終沒能實現。他從未埋怨,反而把這份未竟的心願轉化為推動學生的動力。他想做的,就是搭起一座橋,讓下一代能走得更遠,站得更高,甚至超越他未曾觸及的高峰。
「他們不是我的延伸,而是我真正的成就。」他語氣堅定卻不張揚。
實習結束後,有學生在回程前對他說:「老師,這趟旅程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那句話讓他久久不能平靜。那不是一紙成績單可以衡量的榮耀,而是一種深層的心靈轉向,當一個學生真正看見了世界的廣度與可能性,他也就開始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其中發光。
許教授始終相信,教育不只是傳授知識,更是開啟眼界,是讓一顆心真正相信自己有重量、有光芒、有未來的那一刻。
「如果我能為他們打開一扇窗,那我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他說這話時,語氣平靜卻充滿力量。
他不是要培養追逐頭銜的精英,而是要孕育懂得用雙手去改變世界的年輕人——那些願意用知識去照亮別人生命的青年醫者,才是他心中真正的希望。這份教育者的情懷,就藏在他一句句溫柔叮嚀裡,也寫進每一次替學生點燃未來的起跑線上。



讓台灣,被世界聽見
對許益超教授而言,醫學不只是一門科學,更是一場為人類未來發聲的行動。而「耳朵」,作為最安靜卻也最神聖的器官,早已成為他終生投注的使命核心。2025年五月,他將首度主辦第一屆台灣內耳治療國際研討會,不只是為了聚集國際專家共襄盛舉,更是為了讓世界「聽見」台灣在聽覺醫學上的願景與決心。
他定下的主軸簡潔而深遠:「保健、修復、再生、重建」。這四個詞,背後不是技術清單,而是一份對人類健康尊嚴的承諾,不再等到聽力流失才補救,而是從預防做起;不只延緩病變,更要尋求修復的可能;不只是對症治療,更要以幹細胞與基因療法尋求再生的未來;當一切失去時,還能有重建的科技與希望,重新找回那條通往世界的聲音通道。
「這場研討會,是我們從台灣發出的聲音,」他語氣平穩卻鏗鏘,「我們不只是追趕世界,而是主動向世界宣示:台灣,有能力定義未來的聽覺醫學。」
許教授明白,在國際舞台上爭取話語權,不能只靠熱情,更需要實力、願景與世代傳承。他不僅希望這場會議能讓全球認識台灣的研究能量,更希望激起一波又一波年輕醫師與科研人員的志業熱情。因為這條路,需要的不只是技術接力,更是一群心懷信念的人,願意為沉默的人群發聲。
「我常想,當世界未來再提起這四個詞:保健、修復、再生、重建。他們會不會想到台灣?」他微笑著,語氣裡有一種不容置疑的堅定。
他深知,這場國際研討會不是結束,而是起點。是台灣從過去的技術接收者,轉變為未來的創造者。是一場集結聲音、信念與行動的號角,吹響的不只是醫學進程的下一步,更是台灣主動參與世界醫學對話的歷史一頁。 許教授的語調輕柔,卻藏不住他心中的宏大企圖。他的眼神裡,不只有科學家的專注,更有一位時代布道人應有的光與熱。他相信,一個國家的醫學實力,不只是為了治病,更是為了讓人們不再沉默,讓每一個生命的聲音,都能被世界聽見。




聲音裡,有家的溫度
在實驗室裡,他是研究幹細胞與聽覺再生的專家;在國際會議上,他是論述未來醫學藍圖的講者。但回到家,許益超教授最喜歡的角色,是「爸爸」。
脫下西裝與實驗袍,他換上居家短袖、拖鞋,走進廚房的樣子,親切得就像隔壁大哥。他笑說自己以前是「廚藝零分」,但現在為了家人,什麼都敢試。三杯雞、蒜頭蛤蜊雞湯、麻油松阪豬……一道道料理從零開始,雖然偶爾會被孩子們虧「這鍋有點太創新了吧」,但只要聽到一句「爸,今天這道好吃耶」,他就會開心得像拿了研究計畫補助一樣。
他也常陪孩子出門,一家人最放鬆的時光,就是車上那段音樂小旅行。開車時,他會放著孩子愛聽的流行歌,有時還會跟著節奏打拍子、哼兩句。雖然總是跟不上歌詞、唱得有點跑調,但孩子們會在後座笑成一團,他也跟著笑,笑聲在車廂裡流動,像一首專屬於家的配樂。
假日午後,他和兒子一起去打籃球,球場上你來我往,汗水飛濺。他自嘲現在體力輸兒子一大截,但仍樂此不疲。「他快比我高了,以後可能真的打不贏他了!」他笑著搖頭,那語氣裡有一種含蓄的驕傲。
而每當壓力來襲,或在研究瓶頸前感到力不從心時,他會選擇穿上跑鞋,一個人沿著街道慢跑,聽自己的呼吸、腳步與風聲交織。這種簡單的節奏,能幫他把那些理不清的雜念一點一點地理順。跑著跑著,他會在心裡默念一句熟悉的話:「當你感到疲憊,別忘了你為什麼出發。」
這句話,他不是只對自己說,也是在對多年來那個最初的起點輕聲提醒,那個在電話那端,聲音逐漸模糊的母親。是她的病痛,讓他踏上了醫學之路;是她聽不見的那一刻,讓他開始思考「聲音」的意義。而現在,他守護的不只是耳朵裡的聲音,更是家庭裡的笑聲、飯桌上的共鳴、球場上的叫好與回應。
母親曾為他守住家的聲音,如今,他以科學與愛,延續這份聲音的溫度,在日常裡輕輕擁抱,那些真正值得被記住的,柔軟的時光。

許益超
YI-CHAO HSU, M.D., PH.D.
許益超教授,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主任,專長於聽力醫學與再生醫學。他因母親罹癌的親身經驗,投身於改善聽覺障礙的研究,並致力於開發中草藥與幹細胞技術結合的治療方案。許教授不僅是研究前沿的領航者,更是教育者,帶領學生走向國際。他的願景是讓台灣在聽覺醫學上被世界聽見,並推動保健、修復、再生、重建的全面醫療新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