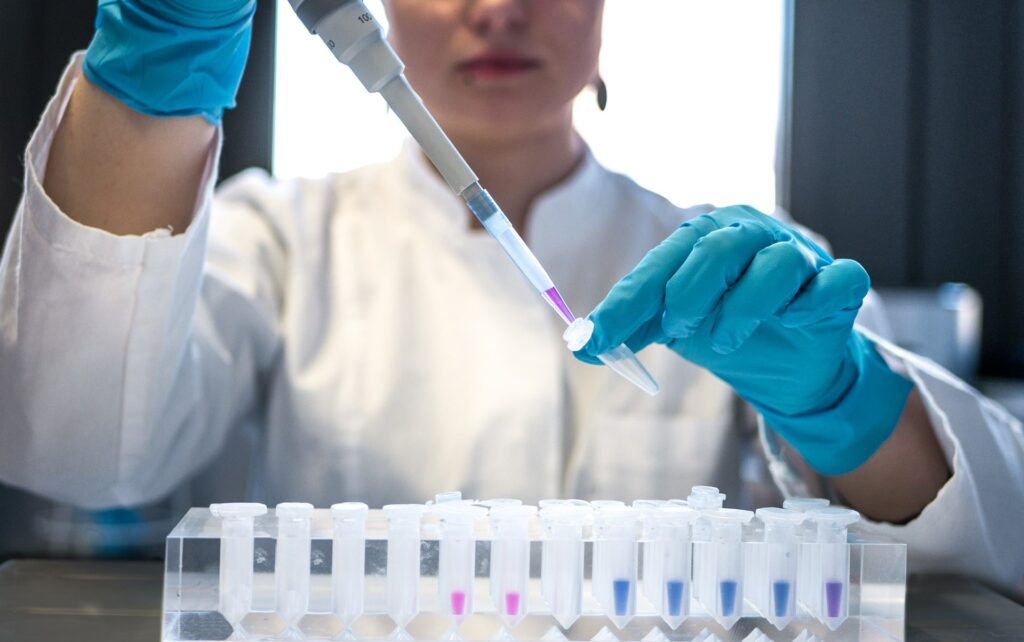
文/ 洪邦喻
新冠疫情一週年,台灣終究爆發了又一次院內群聚感染。理應是好好檢討感控和照護準則的時機,可惜楊前署長「要把染疫醫師開除」的言論轉移了社會的焦點,竟演變成醫界與公衛的再一次惡鬥。那些在防護衣下揮汗的故事,前輩們已經說得夠多,就容我在此蹭個熱度,記錄幾個關於微生物的小故事吧。
疫情期間,父母總是憂慮身在醫院的兒子,而我也總安慰他們「我們把每個病人都當成潛在的傳染源,不必擔心」。事實上並沒有那麼謹慎,防疫也沒有那麼密不透風。醫師們披著白袍走過一床又一床、聽診器接連貼上一人又一人的肌膚,老師們洗手洗得再勤勞,也做不到如OSCE考試般嚴謹。就算戴著口罩,空氣裡還是有著足以同化醫師們腸胃道菌叢的微生物,讓初入醫院的clerk連拉幾週;更別說取下口罩的機會甚多,用餐前隨手折起放入口袋,吃完飯照樣戴回臉上。
尤其菜鳥如我,對風險的認知還太淺薄。第一次進開刀房,看到一張標籤紙從無菌面飄下,便彎腰撿起順手扔掉,結果被護理師念:任何手術台的東西都不要徒手去碰!而就算我不主動犯蠢,在病房還是能與傳染病擦身而過──說是擦身而過或許太保守,畢竟在檢查或發作以前,這些暴露都如同薛丁格的貓,處於感染與沒感染的疊加態。
首先是今年初,學長在閒聊裡告知兩個月前的病人被新診斷出肺結核,護理站詢問他是否要做個X光檢查。據說上面嫌麻煩沒有再打給醫學生,但身為照顧他兩週的primary care,從入院問病史到每天的理學檢查,我和病人的相處時間並不亞於住院醫師。然而在「短期接觸還好吧」的僥倖心態下,這件事就被我擱置了。
再來是前天下班前,接到通知說上個月照顧的病人身上長了疥蟲。這種寄生蟲的潛伏期為二到八週,碰觸病人的衣物、床單都可能沾上蟲卵,無論洗手或酒精都無法有效殺滅。這個月照顧過他的人都被匡列為接觸者,但除了形式上的填表、以及領到一條藥膏備用外,我們什麼都做不了。連忙通知家人用熱水洗過床單和衣服,但如果真的感染,傳播距離早已全不可考。
我不知道三個月遇上兩次傳染病暴觸是否正常,但在醫院工作本就會面臨這些風險,比起針扎、血體液傳染,這兩次插曲完全是微不足道。不過我們僅僅是潛在的受害者嗎?一線醫護的辛勞毋庸置疑,然而自我檢討還是必要的。
醫學生對產褥熱的歷史並不陌生:數百年前的醫師因沒有洗手的習慣,使院內分娩的死亡率高達在家分娩者的數十倍。19世紀的婦產科醫師Charles D. Meigs更聲稱「醫師都是紳士,而紳士的手總是潔淨的」,無數產婦因這種無謂的矜持犧牲了生命。後來溼式刷手法問世,外科醫師開始在上刀前充分刷淨自己的雙手;沒想到近年的研究又表明刷手比乾式消毒液多了細菌在受損表皮繁殖的機會,過去刷到破皮流血的折磨,反而讓病人術後感染的風險提升。
有時候科學證據不夠完備,「為病人好」的思維不見得就萬無一失。美國手術護理師協會(AORN)曾頒布一項指引:為了徹底包覆毛髮和耳朵、避免飄落的皮屑汙染開刀部位,手術室人員應全面使用一次性的不織布頭套。美國外科醫師協會(ACS)為此大動肝火:手術帽是外科醫師的象徵,改成頭套是踐踏我們的尊嚴!眼見又是一次「自尊」的戰爭,不同的是,這次醫師們用證據表明自己才是對的:不織布頭套有較高的微生物穿透性、且使用布帽開刀的感染率並未提升,迫使AORN在新版的指引刪去此條建議。
這是一場微生物和醫護的長期戰鬥。不可否認,院內感染仍然是個嚴峻的問題,醫療人員用盡全力保護自己和病人們,可那裡永遠有著無法填補的縫隙,認真與散漫的醫師都有機會成為受害或加害者。不變的真理是,沒有一位醫護希望自己生病,在這個大家努力奮戰的關頭,還是少說點風涼話,讓他們專心對抗真正的敵人吧。
※註1:會提到「手術帽之爭」的原因是,刀房裡經常可看到主治醫師頭套沒遮到耳朵,而被學生笑稱是「VS自帶無菌效果」;結果文獻一查,發現沒遮到耳朵其實不會有影響。參見Shallwani (2018)、Markel (2017),查詢關鍵字為bouffant cap and surgical skull cap。
※註2:V院允許醫師自備布質手術帽、或使用一次性的不織布頭套,clerk跟刀時大多選擇後者。

本文經洪邦喻授權刊登於《醫學有故事》
原文:醫師與微生物的戰鬥
